多歧亡羊
楊子之鄰人亡羊,既率其黨,又請楊子之豎追之。楊子曰:“嘻!亡一羊,何追者之眾?”鄰人曰:“多歧路。”既反,問:“獲羊乎?”曰:“亡之矣。” 曰:“奚亡之?”曰:“歧路之中又有歧焉,吾不知所之,所以反也。”
楊子戚然變容,不言者移時,不笑者竟日。門人怪之,請曰:“羊,賤畜,又非夫子之有,而損言笑者,何哉?”楊子不答。門人不獲所命。
弟子孟孫陽出,以告心都子。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,而問曰:“昔有昆弟三人,游齊魯之間,同師而學,進仁義之道而歸。其父曰:‘仁義之道若何?’伯曰:‘仁義使我愛身而后名。’仲曰:‘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。’叔曰:‘仁義使我身名并全。’彼三術相反, 而同出于儒。孰是孰非邪?”楊子曰:“人有濱河而居者,習于水,勇于泅,操舟鬻渡,利供百口。裹糧就學者成徒,而溺死者幾半。本學泅,不學溺,而利害如此。若以為孰是孰非?”
心都子嘿然而出。孟孫陽讓之曰:“何吾子問之迂,夫子答之僻?吾惑愈甚。”心都子曰:“大道以多歧亡羊,學者以多方喪生。學非本不同,非本不一,而末異若是。唯歸同反一,為亡得喪。子長先生之門,習先生之道,而不達先生之況也,哀哉!”
“多歧亡羊”譯文及注釋
譯文
楊子的鄰居家丟失了一只羊。這位鄰居已經帶領了他的家屬親友等人去追尋,又來請求楊子的童仆幫忙去追尋。楊子問道:“嘻,丟了一只羊。為什么要這么多人去追呢?”鄰居回答說:“岔路太多了。”
追羊的人回來后,楊子問鄰居:“找到羊了嗎?”鄰居回答說:“沒有追到,還是讓它跑掉了。”楊子問:“為什么會讓它跑掉呢?”鄰居回答說:“岔路之中又有岔路,我們不知道它到底從哪條路上跑了,所以只好回來了。”楊子聽了,心里難過,改變了臉色,很長時間不說話,整天沒有笑容。他的學生覺得奇怪,問他說:“羊是不值錢的牲口,又不是您自己的,而您卻不說不笑,為什么呢?”楊子不回答,學生不知道楊子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楊子的學生孟孫陽從楊子那里出來,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心都子。有一天,心都子和孟孫陽一同去謁見楊子,心都子問楊子說:“從前有兄弟三人,在齊國和魯國一帶求學,向同一位老師學習,把關于仁義的道理都學通了才回家。他們的父親問他們說:‘仁義的道理是怎樣的呢?’老大說:‘仁義使我愛惜自己的生命,而把名聲放在生命之后’。老二說:‘仁義使我為了名聲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。’老三說:‘仁義使我的生命和名聲都能夠保全。’這三兄弟的回答各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,而同出自儒家,您認為他們三兄弟到底誰是正確誰是錯誤的呢?”楊子回答說:“有一個人住在河邊上,他熟知水性,敢于泅渡,以劃船擺渡為生,擺渡的贏利,可供一百口人生活。自帶糧食向他學泅渡的人成群結隊,這些人中溺水而死的幾乎達到半數,他們本來是學泅水的,而不是來學溺死的,而獲利與受害這樣截然相反,你認為誰是正確誰是錯誤的呢?”
心都子聽了楊子的話,默默地同孟孫陽一起走了出來。出來后,孟孫陽責備心都子說:“為什么你向老師提問這樣迂回,老師又回答得這樣怪僻呢,我越聽越糊了。”心都子說:“大道因為岔路太多而丟失了羊,求學的人因為方法太多而喪失了生命。學的東西不是從根本上不相同,從根本上不一致,但結果卻有這樣大的差異。只有歸到相同的根本上,回到一致的本質上,才會沒有得失的感覺,而不迷失方向。你長期在老師的門下,是老師的大弟子,學習老師的學說,卻不懂得老師說的譬喻的寓意,可悲呀!”
注釋
楊子:對戰國時期哲學家楊朱的尊稱。
亡:丟失。
既:不久。率:率領,帶領。黨:舊時指親族,現指:朋友,有交情的人。
豎:小僮,小聽差。
追者之眾 一作:追之者眾。眾:眾多。
歧:岔路,小道。
既反:已經回去。既:已經。反:通“返”,返回,回來,返還。
獲:找到,得到。
奚:怎么。這里指為什么。
焉:語氣詞。
之:到……去。
所以:表示原因的虛詞。
戚然:憂傷的樣子。然:……的樣子。
移時:多時,一段時間。
竟日:終日,整天。
怪:對 感到奇怪。
損:減少。
命:教導,告知。
孟孫陽:楊朱的學生。
心都子:楊朱的學生。
昆弟:兄弟。
齊魯:均為春秋時期諸侯國名,指今山東一帶。
伯:兄弟排行第一,老大。
仲:兄弟排行第二,老二。
叔:兄弟排行第三,老三。
泅(qiú):浮水,游水。
鬻(yù)渡:渡船謀生。嘿然:默認。嘿:同“默”。
讓:責備。
嘿(mò)然:默然。嘿:同“默”。
喪生:喪失本性。“生”字,不能夠機械地只理解為“生命”,而還要理解為“性”字,當“本性”講。
歸同反一:回到相同的道路,返回一致的道路。
況:比喻。
“多歧亡羊”鑒賞
寓意
列子這篇寓言在結構上很有特色,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復合寓言的方法。羊寓言故事本身從這個寓言引出另兩個寓言,一個是心都子講的三兄弟同學儒術領會卻完全不同的寓言,另一個是心都子講的眾多人學泅水近半數人溺死的寓言,最后是心都子的評論。一些寓言選本,對這篇寓言往往只選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,而不選從這個故事引出的后兩個寓言故事,更不選最后的心都子的評論。但這種節選的做法,并不是很妥當的。因為只從歧路亡羊故事本身,是不能直接領會到,至少是很難領會到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。
讓我們先來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。在這個故事中,楊子的鄰居的羊逃跑了,已經有家屬親友等人去追尋,還覺得人不夠,又來請求楊子的童仆幫助去追,結果還是沒有追到。為什么呢?因為岔路太多,岔路中間又有岔路,不知道該從哪條岔路去追,所以這么多人去追,還是追不到。楊子對這事感觸很深,很長時間不言不笑,他的學生問他為什么這樣,楊子竟然沒回答。
從整篇寓言看,當時楊子沒有回答學生們的疑問,是因為楊子對歧路亡羊一事,感觸很深,一時難以對學生們解釋清楚,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,特別是寓言這種高級譬喻的形式,才能使學生們明確無誤地領會到其中所蘊含的深刻的寓意,這也就是楊子對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。
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話“大道以多歧亡羊,學者以多方喪生。學非本不同,非本不一,而末異若是,唯歸同返一,為亡得喪。”表達了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。“大道以多歧亡羊”一句是對“歧路亡羊”故事本事的概括;“學者以多方喪生”既是對眾多人學泅水近半數人溺死故事的概括,又是對三兄弟學儒術領會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(這里“喪生”的“生”字,不能夠機械地只理解為“生命”,而還要理解為“性”字,當“本性”講,“喪”生也應當作“喪失本性”。理解前一個故事和后兩個故事之間,有非常密切的聯系,這就是,前一個“大道以多歧亡羊”故事是用以比喻“學者以多方喪生”的,意思是:求學的人經常改變學習內容、學習方法,就會喪失本性,迷失方向,甚至喪失生命,只有抓住根本的東西、統一的本質的東西不放,才不會誤入歧途。寓言中心都子的話“學非本不同,非本不一,而末異若是”。曾被西晉人盧諶用為典故,寫在他的《給司空劉琨書》中:“蓋本同末異,楊失興哀。”這兩句話中“本同末異”是心都子的話“學非本不同,非本不一,而末異若是”的濃縮;“楊朱興哀”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楊朱聽說此事后心里難過,長時間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,毫無疑問,這兩句話是出自列子的這篇寓言。有的學者認為不是盧諶這兩句話出自《列子》,而是偽作《列子》者,以盧諶的這兩句話為素材,并根據這兩句話偽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。乍一看,盧諶引用《列子》和偽作《列子》者根據盧諶的這兩句話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,兩種可能都有。這兩種可能互相矛盾。一種是真的,另一種就必定是假的,究竟哪一種是真的,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。
還有一種說法就是“或當時古書已有比章(偽)作《列子》者用之也”,這是一種“想當然”“也許有”的說法,從古代的文獻記載和傳世文獻看,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評論,均僅見于《列子》而不見于他書,如盧諶當時已有此事,也只能是《列子·說符》中記載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評論的這一章,但持《列子》偽書說者,卻偏偏不甘心承認,說什么也許有別的古書有此章,偽作《列子》者引用了這個故事,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。沒有根據卻硬要這樣說,只不過是“遁辭知其所窮”罷了。
求學的人經常改變學習內容、學習方法,就會喪失本性,迷失方向,甚至喪失生命,只有抓住根本的東西、統一的本質的東西不放,才不會誤入歧途。
從這篇寓言,我們還可以進一步領會到,不僅學習上要緊緊抓住根本的東西,一致的本質的東西,觀察和處理一切事物都應該這樣。客觀事物錯綜復雜,干什么事情,都必須專一,不能三心二意,見異思遷。如果毫無主見,見到岔路就想另走,那就會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誡的那樣,到頭來是會一無所獲甚至會有喪失本性甚至喪失生命的危險的。
由這篇寓言凝煉而成的成語“歧路亡羊”、“多歧亡羊”,比喻因情況復雜多變或用心不專而迷失本性、迷失方向,誤入歧途,一無所成,后果嚴重。如明馬中錫《中山狼傳》中說:“然嘗聞之,大道以多歧亡羊。”清初王夫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中指出:“而諸儒之言,故為糾紛,徒俾歧路亡羊……一字不審,則入迷津。”
告訴人們:在研究一門學問時,要把握方向,注重領會其實質,而不要被各種表象所迷惑。
列御寇簡介
先秦·列御寇的簡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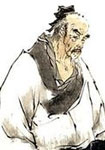
列御寇,名寇,又名御寇(又稱“圄寇”“國寇”),相傳是戰國前期的道家人,鄭國人,與鄭繆公同時。其學本于黃帝老子,主張清靜無為。后漢班固《藝文志》“道家”部分有《列子》八卷,早已散失。
...〔? 列御寇的詩(4篇)〕猜你喜歡
鷸蚌相爭
趙且伐燕,蘇代為燕謂惠王曰:“今者臣來,過易水。蚌方出曝,而鷸啄其肉,蚌合而箝其喙。鷸曰:‘今日不雨,明日不雨,即有死蚌!’蚌亦謂鷸曰:‘今日不出,明日不出,即有死鷸!’兩者不肯相舍,漁者得而并禽之。今趙且伐燕,燕趙久相支,以弊大眾,臣恐強秦之為漁夫也。故愿王之熟計之也!”惠王曰:“善。”乃止。
虎求百獸
荊宣王問群臣曰:“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,果誠何如?”群臣莫對。
江乙對曰:“虎求百獸而食之,得狐。狐曰:‘子無敢食我也!天帝使我長百獸。今子食我,是逆天帝命也!子以我為不信,吾為子先行,子隨我后,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?”虎以為然,故遂與之行。獸見之,皆走。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,以為畏狐也。
今王之地五千里,帶甲百萬,而專屬之于昭奚恤,故北方之畏奚恤也,其實畏王之甲兵也!猶百獸之畏虎也!”
孟母三遷
鄒孟軻母,號孟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時,嬉游為墓間之事。孟母曰:“此非吾所以居處子。”乃去,舍市旁。其嬉游為賈人炫賣之事。孟母又曰:“此非吾所以處吾子也。”復徙居學宮之旁。其嬉游乃設俎豆,揖讓進退。孟母曰:“真可以處居子矣。”遂居。及孟子長,學六藝,卒成大儒之名。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。
曾參烹彘
曾子之妻之市,其子隨之而泣。其母曰:“女還,顧反為女殺彘。”妻適市來,曾子欲捕彘殺之。妻止之曰:“特與嬰兒戲耳。”曾子曰:“嬰兒非與戲也。嬰兒非有知也,待父母而學者也,聽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,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,子而不信其母,非所以成教也。”遂烹彘也。
(選自《韓非子.外儲說左上》)
師曠撞晉平公
晉平公與群臣飲,飲酣,乃喟然嘆曰:“莫樂為人君!惟其言而莫之違。”師曠侍坐于前,援琴撞之。公被衽而避,琴壞于壁。公曰:“太師誰撞?”師曠曰:“今者有小人言于側者,故撞之。”公曰:“寡人也。”師曠曰:“啞!是非君人者之言也。”左右請除之。公曰:“釋之,以為寡人戒。”